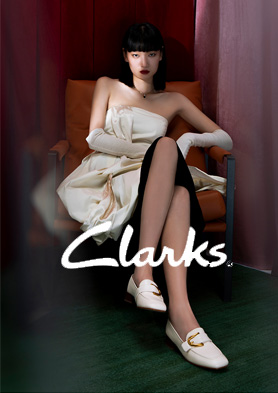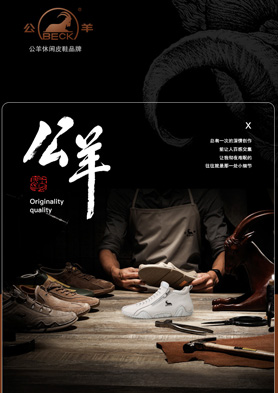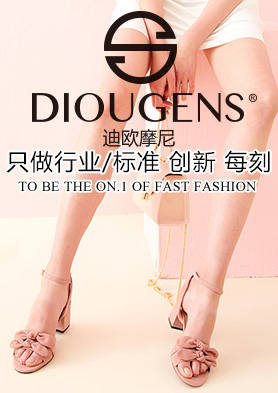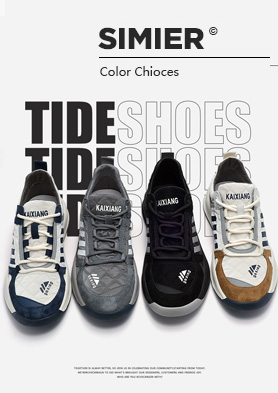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CPI影响有限
自去年以来,有30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省份的调整幅度都在10%左右,一些地方甚至达到25%以上。今年初,全国各地又掀起新一轮的“加薪潮”。在江苏率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上海、山西、重庆、浙江等省市也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与此同时,我国物价指数一路飙升。从去年开始,CPI不断冲高,今年也一直延续去年的涨势,一季度涨幅高达5.4%。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会否对本已高高在上的CPI带来更大的上涨压力?缓解物价高企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除调高最低工资外,是否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对物价指数影响有限
对于各省市“涨薪潮”对CPI的影响,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表示并不认可这个观点。在采访中他告诉商报记者,上调最低工资必然会使企业生产成本加大,受此影响,CPI会有上升压力。但应该看到,CPI还包括很多构成要素,如公共交通费用、居民菜篮子花费、租房费用、看病费用等等各种重要生活资料价格都位居其中,工资只是其中的一项。所以,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对CPI影响有限。
他甚至乐观地表示,如果企业能够抓住此次机会转变以往粗放的发展方式、调整产品结构,加强自主创新和管理的同时提高企业效率的话,企业其他生产成本完全有可能下降。这样,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CPI的压力就可以被冲减抵消甚至整个物价成本有可能反而下降。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该问题上也表现出类似立场,他告诉记者,CPI指数的上升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没有必然联系。目前,国内高企的CPI主要还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近两年国内货币的过度发行导致流动性泛滥,巨额的外汇储备与银行贷款也是推手。其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国内致使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PPI指数从而不断抬高。
在胡星斗看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主要是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通胀压力对民生造成的影响。“为了缓解中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才采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来舒缓民生困境。”
高薪阶层不应借机涨工资
事实上,多省市此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初衷主要在于缓解不断上升的物价水平给中低收入阶层带来的种种压力。然而,坊间对此的一个普遍担忧却是,一些国企的高收入者和管理阶层会不会借机搭车大幅提高本已不低的工资待遇。
这个忧虑同时也是胡星斗的担心所在。在采访中他告诉商报记者,在这之前与民生相关的机制体制改革中都出现过类似的“状况”,一些改革的初衷本来是为百姓民生着想,但到了最后,反而是一些高收入高消费的权贵阶层获益最多。
“在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内部或者不同企业之间,工资收入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一些国企完全有可能借机给管理层大幅涨薪,并不会顾及基层员工。”胡星斗如此表示。他建议,在此轮改革过程中,应该防止部分国企借机不合理涨工资,同时应该缩小企业内员工的工资差距。其次,国家应该降低资本所得,提高劳动者收入。
沈骥如也对记者强调,应该坚决杜绝垄断企业巨额利润用于本企业高管薪水待遇的提高。长期以来,我国不同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对拉动内需发展经济无益。此外,如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不能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话,对社会稳定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保障低收入群体收入
回到“物价高企对低收入群体产生的影响”这个原点上,民众似乎更关心的是,除了调高最低工资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更为可行与民众接受程度较高的解决办法?
对此,胡星斗表示,最常用的办法还是对低收入者进行补贴,货币补贴或必需生活资料的实物补贴。其次,应该对国企净利润进行全民分红,或者将其上缴给国家财政用以弥补养老金的不足。同时,政府还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提高劳动者地位,保障其权益,比如谈判、
集体协商等,用机制体制保证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主任刘澄则建议,在CPI高涨时期,政府应该运用《反垄断法》对国企进行价格管制,对国企员工收入也进行合理的收入管制,在适当时候可以冻结其收入。另外,金融机构应该加强货币的回笼,适当提高利率。最后,应该开辟融资渠道、改善实体领域投资环境,让资金适当回流到生产领域,控制流通领域的不合理炒作。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目前将中低收入者工资待遇的改善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日前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努力实现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职工工资增长15%,5年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也表示,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这个基本原则下,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幅度应该是更高更快,这才能缩小收入差距。这一切都意味着,低收入阶层的“荷包”未来肯定会越来越“鼓”。 (来源: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