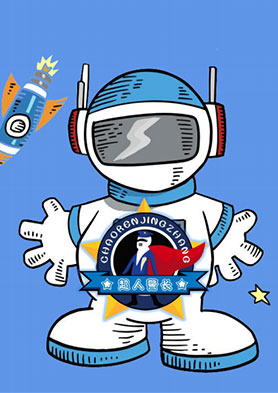产业转移之痛:广东该往何处去

4月17日,广交会鞋类交易区外商稀少、门可罗雀。 本报记者卢汉欣摄
人民币首度“破七”,令正在举办的广交会备受各方关注,纺织、鞋业、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订单下滑早在人们意料之中。事实上,珠三角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成千上万的工厂面临关闭潮,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企业正在计划迁离这里。昔日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会不会成为历史?在时下高压、躁动、犹疑、对峙交织的阵痛中,广东正站在裂变的十字路口。
在广东这块土地上,可能有几百万个潜在的“马云”,关键是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机制,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
南都:作为一个商学院教授,你曾经对的吸引外资政策和本土企业状况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察和研究。那么,你现在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发起了“实验室”项目,来帮助的小型创业企业,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来设立这个实验室的?实验室的具体运作又是怎么样?
黄亚生: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目前的民营企业在数量上非常巨大,但质量却普遍低下。根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的调查数据,有几个指标很能说明问题:员工培训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仅有1%左右,更有25%的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入是零。2000年后,的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企业科技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并没有随之增加。举个例子,现在广东面临劳动成本提高、原材料成本提高等挑战,如果企业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和管理,再有自主创新能力的话,它就能消化这个挑战。让我们看看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当时他们都碰到类似问题,什么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提高等等,但他们比较好的企业并没有因此丧失竞争能力,反而抓住机遇,成长为大型跨国公司。丰田汽车在上世纪80年代时还在生产低档汽车,并不比今天的奇瑞强,但在日元升值以后,丰田马上在产品上进行革新,推出了雷克萨斯等高档产品,从而实现自己的升级转型。相比之下,我们的企业显然没有日韩企业当年的那种应变能力。我在MIT一直是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我常问自己,能否做点什么,来帮助的中小企业提高它们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创新,主要是靠中小企业。这就是发起实验室的最初想法。
我在MIT商学院的学生其实是个巨大的资源,他们大多不是本科毕业就来读书的学生,是已经有了几年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年龄二十七八岁,而且他们不少原先工作的地方是像麦肯锡、高盛这样世界一流的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他们在我这边上学,我有两年的时间免费使用这些资源,实验室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可以给的中小企业免费提供培训。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7年,至于挑选企业的标准,有的是通过比如与我们合作的复旦大学商学院的校友推荐的,有的是我熟悉的某些风险、私募基金投资的企业,但都是近来成立的创业型公司,今年有20家申请,我们只选择了其中12家,广州也有3家。我们对通常认为的高科技企业并不最感兴趣,我们更看重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企业,比如这次有杭州的一家做社区医疗的公司,有广州一家做经济型连锁酒店的公司,还有在昆明做家具和支线航空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中小企业认识到商业管理对他们的价值。
南都:作为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中小企业的数量、产值一直居全国之首。但是,目前广东的中小企业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前段时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江浙考察时还亲自去杭州拜会马云,力邀马云来广东合作,开辟广东市场。你怎么看待马云现象?在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方面,政府能做些什么?广东又有那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黄亚生:为什么好的私营企业都出在浙江?马云刚开始创业是在上海,他觉得上海经营环境不好,才跑到浙江。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政府最好不要去做干扰企业运作的任何事情,只要把当地的经营环境做好就可以了:比如取消复杂的审批手续,不要去打压个体户,在金融上对中小企业提供一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一些贷款担保,等等。至于邀请马云来合作,可能更多地是一种姿态。马云不是拉过来的,而是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他自己成长起来的。
我们应该这么去看待马云现象,上海没有留住马云,也许是个个案,但没有留住马云,为什么也没有产生刘云、李云、赵云呢?这就是体制和环境的问题了。广东应该这么去看待马云现象:在广东这块土地上,可能有几百万个潜在的“马云”,关键是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机制,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否则,即便是马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你让一个官员去判断,此人10年后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他肯定是判断不出来的。我也判断不出来。马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最终要靠市场来决定。如果是市场运行的话,自然有马云脱颖而出。我觉得,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吸取浙江模式的经验,给予企业更多的经济自由。
南都:资金匮乏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那么,英法美日这些走在前面的国家,他们对推动中小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有些什么扶持政策?他们的中小企业融资手段主要有哪些?
黄亚生:这些国家对中小企业的重视,其实就体现在我刚才讲到的就业,西方民主国家非常重视就业,而就业主要就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大企业的银行贷款通常是不提供担保的,但会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些风险担保。而在恰恰相反,政府只给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提供贷款担保,小的企业不要说担保,反而还会限制银行对他们的贷款。
现在学术界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保护中小企业,不仅能促进就业,还能促进技术进步。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绝大多数的创新来自于中小企业。硅谷,我们在经常提这个词,但从来没有人研究“硅谷”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从硅谷里面成长出来的巨人,刚开始都是个体户。现在的微软是一个IT巨人,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但是,微软在1975年是个什么公司?就是一个个体户,两个没毕业的大学生去创业。等到微软变成世界500强之后,它很多创新技术都是通过收购小公司获得的。中小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带来就业,二是带来竞争,三是大企业的知识创新动力普遍很弱,需要通过收购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来获得创新能力。
反观上海的做法,是把小企业全部赶走。有一次我和上海的官员聊天,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回答冠冕堂皇,产品需要更新换代。我就继续问,什么叫产品更新换代?举个例子,一个是生产纺织品的工厂,一个是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你如果让一个官员作判断,哪个是高科技产业?他肯定会回答,当然是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事实恰恰相反,现在纺织品生产的科技含量到什么程度?法国一家生产运动衫的企业,雇佣MIT的生物学家做产品设计,研究当人体出汗时,这个产品对人的身体有什么反应,技术含量非常之高。而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技术含量反而非常低。如果让市场上的那些纺织企业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它们自然会向高科技这方面发展的。但现在政府一下把他们全部关停赶走,官员取代了市场,它们就丧失了转型发展的机会。
黄亚生教授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1987-1989年任世界银行顾问,1991年获哈佛博士学位之后任密执安大学助理教授,1997-2003年任教哈佛商学院,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199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学院)。
- 上一篇:“奥运概念”领跑“中国鞋都”晋江
- 下一篇:关税重压下,仍有中国鞋服跨境电商逆势增长